他曾經鑒定上海博物館藏的王淵(13世紀末一14世紀中期)《竹石集禽圖》,從畫面的時代特點與個人風格來看,可以肯定是王淵的晚期作品。其次看其隸書款和“王若水印一墨妙筆精”二印,鈐印很好,紙張也符合時代面貌。再考究它的流傳經過,解放前為上海周湘云所有,畫上的“張弧之印”則表明它曾為張弧舊藏。乾隆皇帝的印璽則說明它曾庋藏于清內府,入內府前又經梁清標收藏,因為其上有“棠村審定”“蕉林”二二印。后看“八年癸丑”的年款,宣德八年(1433年)正好是癸丑,上距作畫時間約一百余年。作品的主要依據和輔助依據均一致,于是可以斷定它是真跡無疑。他的鑒定理念對其后的謝稚柳、徐邦達等人有著深刻的影響,這二位鑒定家對張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與運用,自成一格。綜觀20世紀中國書畫鑒定界,張珩對于書畫鑒定學具有開山之功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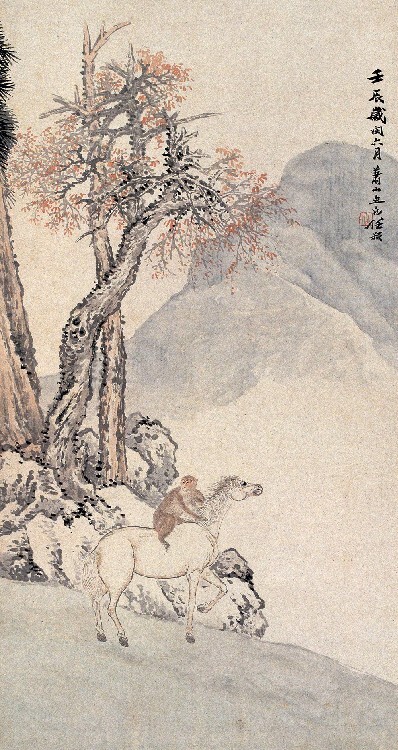
謝稚柳
先生工詩文,能書法,擅山水、花鳥,亦偶作人物,尤精書畫鑒定,與張珩并稱“北張南謝”。謝先生早年學畫,又與張大千一起對敦煌壁畫進行了長期的研究,這使他準確地把握了唐宋以來中國書畫主流風格的淵源流變,由此確立了以風格流派斷代,辨偽的方法。正如他本人所說“切實的辦法是,認識從一家開始,而后從一家的流派淵源等關系方面漸次地擴展”。雖然他也不忽視對相關文獻的印證,但卻更看重書畫藝術的本體,如作品的意境,格調、筆法、墨法、造型和畫面布局等特征,即
重視書畫本身的體貌精神
四是極為傾心梳理見于著錄的
。下僅舉徐先生通過筆墨鑒定書畫的個案,以窺其鑒定之一斑。筆墨與毛筆的特點與性能有關,宋代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中載:“熙寧后始用無心散卓筆,其風一變。”而傳世的晉王珣的《伯遠帖》,其字筆畫吸墨不多,轉側也不靈活,轉折時往往提筆再下,分明用的是無心筆,此帖必贗本或臨本無疑。再看唐代孫過庭的《書譜序》、僧人懷素的《苦筍帖》、顏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、杜牧的《張好好詩》等大都使用一種堅硬而吸墨不多的有芯筆,若用無芯軟筆定當無此效果。而傳為王羲之的《大道帖》(臺北故宮博物院藏),其筆畫潤豐圓熟,含墨極多,用晉代的有芯筆是寫不出來的,所以定為宋代米芾的臨寫本。徐先生著述宏富,已逾500萬字,近期由故宮博物院出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