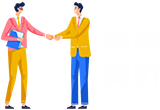文史知識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,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,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。
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,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,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,又換了個新皇帝,有的就改了元,即換了年號,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,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: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,是萬歷四十八年(1620)七月死的,八月朱常洛(光宗)做了皇帝,改元泰昌,僅一個月就死了,九月朱由校(熹宗)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,直到下一年(1621)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,萬歷只有47年,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:朱由檢(毅宗)是崇禎十七年(1644)三月死的,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
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,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均是符合邏輯的,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,則不符合邏輯,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,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,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,同樣是符合邏輯的,例如: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: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,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,以為崇禎只有16年,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
在書畫鑒定中,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(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)與避家諱(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)兩種。在鑒定學中,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,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。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: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(多為后一筆),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,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。例如: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《千字文》卷,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,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,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,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,該卷本幅確為宋紙,并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,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。后來又發現該《千字文》"紈扇圓"的"紈"字被改寫為"團"字,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(因"紈"、"桓"讀音相近而避諱)。考黃庭堅寧四年(1105)卒,距欽宗靖康元年(1126)還有21年,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,因此,肯定了這卷《千字文》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。
又如:約50年前,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,畫得很好,落款字數不多,作品本幅十分整潔,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,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,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,沒有活到清代,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,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,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,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,那么,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,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。
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,所以比較細;嘉、道以后拖尾長,卷子就粗了。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,手法亦異。熟悉了以后,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、何地的裱工,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,手藝相當高超,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,仍能裝裱如原裝。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裝裱后,如果懸掛或正視,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。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,則原形畢露。所以,如果遇到裱得很厚,或者裝在鏡框之內的書畫,就一定要特別注意。
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,保留原裝裱,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。鑒別這類書畫,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偽了。
曾經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。一般人來看,確實是宋朝的畫,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。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,組成了一幅新的畫,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,蒙了很多人。現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,把古畫拼接、嫁接、挪位,很有隱蔽性。
從顏色上講,明末清初出現的泥金紙為赤黃色,到清代后期,泥金紙變成了淡黃色。
清康熙至嘉慶,出現了一種粉箋和蠟箋紙,劉墉、黃易、梁同書等人常用,清末吳大溦則用日本紙作畫。
此外,紙還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和新舊之別。一般講,早期的紙,尺寸較小,后期的紙尺寸越來越寬
對紙的質料,紙的型制,還有絹和綾的各個時代特征要熟悉。
例如,清康熙、乾隆以來流行彩色粉箋、蠟箋紙,上面還描上金、銀花紋,只能寫字,不宜繪畫。
還有明末天啟、崇禎或稍后一段時間,流行一種素綾,在書畫上常用,尤其書法條幅用得多,到晚清時還有人使用。
對這些特殊的現象也要全面了解。關于紙、絹及綾,有作偽者常將紙、絹作舊見利
對于做舊與原舊要區別開來。原舊有一種自然老化產生的“包漿”光亮,而作舊是用顏色、茶水、臟水染舊,或油煙薰舊。
(一)絹,大約唐、宋的書畫都用絹,元以后用紙越來越多。用絹、綾鑒定書畫,僅從制作規格上看,極難區別其生產的年代.
如拿清康熙時的“貢絹”與南宋時的院絹比較,除新舊氣息不同外,形制方面幾乎一樣。故不能把它作為斷代的依據。
但絹的門面尺度和砑光卻有時代的不同。從傳世每幅絹的門面看,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絹闊大都不超過60厘米。
宣和以來,則逐漸放寬,有幅畫軸闊至80厘米的,如趙佶《芙蓉錦雞雞》(幅81。5厘米)。
到南宋中期,已有一米以上門面出現,如李迪《楓鷹雉雞圖》,闊至105厘米。絹除門面外,還有砑光的問題。
從年代講,砑光絹到明末已有,絹地光亮而薄。至于用砑光絹作畫,到咸豐、同治以來的書畫中方能見到,此可用作為斷代依據。
(二)綾,傳世中有花綾和素綾兩種。前者唐貞元以后,誥(來+力)用花綾。
后者在明成化、弘治時沈周等人的作品見到。到天啟、崇禎時則廣為流傳。所見為王鐸、傅山等人的書法卷軸為多,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見了。
絹、綾的單絲和雙絲不能作為斷代的依據,因為它們沒有明顯時代劃分。而絹綾精粗程度可為書畫的斷代提供佐證。